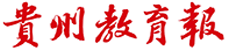冬至一阳生,万物待新生
福泉市第三中学七 (9) 班 李荣张
早晨推开窗,霜气如碎玉般落在肩头,寒意浸骨却不刺骨——老人们总说“冬日一阳生”,这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竟然有着最温柔的新生密码。“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在耳畔回响,奶奶总打趣说这是长辈骗小孩吃饭的巧思,可那蒸腾的热气里,分明裹着对阳生萌生的满心期盼。
小学时总是不懂,为什么最冷的时节偏要称“阳生”? 后来在古籍里读到“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才懂古人早已从日影的微末变化中,捕捉到天地的玄机:冬至的夜虽长,却是此后逐渐缩短的开端,正如杜牧笔下“他乡正遇一阳生”,即便身在天涯,也能从光影流转中触到时光回暖的轨迹。
院里,冬至物候间藏着“藏”与“生”的默契。老梅树褪去繁叶,花苞在枝丫间悄悄蓄红,恰应朱淑真“梅花先趁小寒开”的诗意,只待一场雪落就绽放暖意;屋檐下麻雀啄食的蓬松绒毛,是抗寒的铠甲,也是迎阳的准备;墙角苔藓在薄冰下凝着深绿,将最后一丝湿润酿成来年生机。奶奶扫着阶前的霜雪说:“霜是土地最好的棉被,好让阳气慢慢钻出来。”“冬至冷,明春暖得早”的老话,道尽万物蛰伏的智慧——最冷时刻恰是新生序章。
奶奶总说“冬至大如年”,这天要祭祖、包饺子,还要给我缝绣有太阳纹的大棉袜,针脚细密如时光纹路:“穿了冬至袜,冻不着脚丫,还能跟着阳气长个儿。”这些细碎习俗里,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他们把希望揉进汤圆、包进饺子,让冬至成为连接过往与未来的纽带。
这样的日子最适合围炉读诗。白居易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让我想起了奶奶给我下汤圆,在我手心画太阳,念叨祝福,香甜混着柴火气烘暖寒夜。
冬至的寒,冻不死种子的梦,却让它在泥土里扎下深根,静静等待春阳唤醒的那一刻——这“一阳生”的暖意,早已刻进我们的生命里。
指导老师:尚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