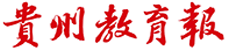花开的岁月
■ 杨鸿飞
今年三月,我住德江,这里油菜花开得特别旺,妻子说出去走走,我们便高兴地出了门,在德江县合兴镇,我们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在春风中翻涌着,形如沉在河底的琥珀,正招引无数游客来这里驻足观赏。
春风吹拂,油菜花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似仙女般柔嫩,在微风的抚摸下舒展着她那轻盈的舞姿不停地在空中摇摆。阳光浇在花上,每片鹅黄泛着绸缎般光泽,连叶片都镀着金边儿。花茎轻颤,千万朵花儿又像提着绿绸裙摆的村姑,在齐腰的叶浪间跳起圆舞曲,加上甜津津的香气裹着细沙般的花粉簌簌落进衣领,连呼吸都染上了春的味道——这是土地写给春天的情书,每笔都蘸满了阳光的温度。
我和妻子来到观景台,看到前来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姑娘索性提着雪纺裙蹲在花海里,同伴抓拍发梢沾着花瓣的瞬间,露出灿烂的笑容。妻子想找一个高地一览菜花美景,我却偏爱独自走进深处感受童年时光,每当鞋尖拂过披露的草茎儿,一两只蓝蜻蜓掠过花穗,抖落几点星星花粉,更让人陶醉。我蹲下身才看清每朵花都是精致的小喇叭,五片花瓣薄如蝉翼,托着嫩黄的花蕊,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指尖刚触到花茎,凉丝丝的触感混着青草香涌了上来。忽然,我想起父亲粗糙的手——那年我执意要摘花,他握住我的手轻轻摇头说:“花开是攒了一冬的劲儿,你轻些碰,别惊了它们!”我凑过去让鼻尖埋进花球,任由甜香漫过整个胸腔,恍惚间又回到了他背着我,走过田埂的时光。
眼前的油菜花在枝头轻轻摇晃,然而我记忆里的时光早已回到20年前的冬月。那时,田埂上飘着雨丝,父亲弓着背用铁锨翻土,铁锨与石块相撞发出“当啷”声,惊飞了躲在枯草里的田鼠。我和妹妹蹲在旁边播撒菜籽,指尖捏着比芝麻还小的种子看它们钻进湿润的土缝,像撒一把星星在泥土。母亲挑着粪桶裤脚沾满泥点,她却说种下菜籽就是种下希望,等开春漫山金黄,日子也就好过了,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希望,只记得腊月里去田边看菜苗,嫩绿的小菜芽刚破土像婴儿的睫毛,在料峭的风里抖抖索索十分可爱,它们倔强地朝着天生长。
每年正月,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盼望闹元宵,因为在家乡有一种风俗叫“排油姻”。夜里,湛蓝的天空挂着一轮美丽的圆月,我们几个就趁着皎洁的月光往油菜地里跑,绿绿的油菜叶在月亮照耀下泛着点点青光,像铺了一地的绿毯。大人说在菜地里跑上三圈,霉运就像菜叶上的露水一样在天明时消散得无影无踪。于是,每年的元宵月夜,一帮小孩子在油菜花地里穷追着彼此的影子,也惊飞了躲藏在菜地里的夜鸟,现在想起确实有些天真,当时也不知道踏坏了多少油菜。跑累了就蹲在地里掐菜薹儿,凉津津的茎叶在掌心攥出青汁,带回家用滚水一焯,拌上粗盐就是最鲜美的春菜。
家乡的油菜花最盛时也是在三月,三月里,整个村子都泡在香海里。我和芳芳姐喜欢躲在齐腰高的花田里唱 《九九女儿红》,金黄的花穗挡住视线,只能看见对方头顶晃动的花球,笑声撞在花瓣上,又弹回成细碎的光斑。有时唱累了,就躺在田埂上看天,白云从花尖上飘过去,花瓣落在鼻尖痒痒的,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朵花,跟着风摇晃在春天的掌心里。一到这段时间,母亲常在田间拔草,几个月来,她一直穿着的蓝布衫让我印象最深刻,阳光下,她的影子被花穗切成碎块,却总能准确叫出我们的名字:“别躺太久,当心菜虫爬进脖子。”那时我不懂她话里的重量,直到看见父亲在煤油灯下算收成:三亩地,亩产200斤菜籽,每斤能卖八毛钱。他粗糙的手指在纸上画下歪歪扭扭的数字,算完大妞的学费,又给二娃添双新鞋,最后剩下的,要留着买开春的化肥——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株被风雨压弯的油菜,却始终朝着光的方向。真正懂生活分量的是每年“五一”小长假,也是我们的收割季。天还没透亮,母亲就第一个起床,接着就是父亲的声音,大家喂猪的喂猪,煮饭的煮饭,磨刀的磨刀,吃完早饭,一家人全都赶到田里去割油菜籽。只要弯腰割上半亩地,腰杆就像被人打了一棍,直起时眼前发黑,只能扶着膝盖喘气。妹妹的手被菜茎划出血痕,却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流血的手指往裤腿上一擦,继续低头割,裤腿上很快洇开暗红的小点。父亲总走在最前头,他的蓝布衫被汗水浸成深色,脊梁骨在衣服下凸起如老树根,却始终比我们快上两垄,镰刀过处,菜秆整齐地倒在泥地上,像给土地织了床金毯子。
天渐渐暗了,父亲停止手中的劳作,一个人蹲在田边不住地抽着旱烟,眼睛盯着远山发呆,他那厚厚的嘴唇伴着烟嘴随一明一灭的火星不停地动:“等你们考上大学,我就不再吃这苦了。”
我知道这是父亲在自我安慰,心里也就乐滋滋的。夜色和着烟雾模糊了他的脸,在他那手腕上,被菜汁染黄的老茧却让我瞬间觉察到父亲那被汗水泡透的日子,每一滴汗都化成了他肩膀上的红疤。记得油菜成熟时,父亲每年都要挑百多斤菜籽去镇里,一路上竹扁把他的肩压得通红,扁担发出吱呀声和心跳声合着拍子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后来,我进县城读高中,在城郊看到了比家乡大几十倍的油菜花地,当地人称它为“油菜村”。花开时节,油菜花成了郊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慕名而来的游客将一辆辆旅游大巴车停在新修的水泥路上,在油菜花地里,他们举着自拍杆在花海里穿梭。可我却没时间看花儿了,大半时间只是蹲在花开的地方背背书。傍晚,夕阳把花穗染成金红色蜜蜂在耳边嗡嗡地飞,衣兜里攥着母亲用罐头瓶送来的菜油炒的辣椒,那香味儿直接让人吞口水。打开瓶盖儿,那油汪汪的辣椒上还飘着几粒没滤净的菜籽,也许,这就是土地最慷慨的馈赠吧! 我知道这片花海不仅是颜料,更是翅膀载着我们姐弟飞出了黄土地,我们却把根永远留在了这金黄的梦里。
时过晌午,观景台上的人不断变换面孔,在来来回回的游客中间,我没有徘徊,我和妻子沿着油菜花地小道来到立着“生态农业示范园”的牌子前,风来了,带着熟悉的甜香漫过田野。远处传来游客的惊叹,可我听见的却是岁月的回声——仿佛父亲翻土时铁锨撞击石块的声响,又像是母亲在花田里哼的民谣,如我们姐弟割菜籽时镰刀与茎秆的私语,似土地对耕耘者最绵长的告白。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时光里酿成了一首长歌。
(作者单位:德江县思源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