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学政三年锐意改革创新
严修:引领贵州人开眼看世界
 |
 |
| 严修像 |
 |
| 位于南开校园内的严修铜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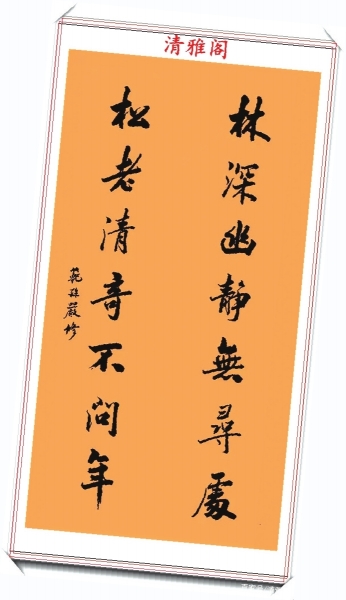 |
| 严修书法作品。 |
严修如果能看到《清史稿·选举志》这本书,他大概率会自谦地说“过奖了”,因为他是这本书中唯一一位被三次提名的人物。其中第一次提名,是因为他在任贵州学政时所立下的功劳。
《清史稿》对他的三次提名,勾勒出严修在晚清学务改革中的独特地位,也彰显了他的视野与气魄。
严修(1860年—1929年),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直隶天津(今天津)人,祖籍浙江宁波慈溪。严修早年入翰林,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
京官授命赴黔任学政
如果真有文曲星,那么严修跟他的关系一定很铁,早年的严修就是一个学霸。严修24岁那年,就通过了皇帝主持的殿试,中了进士,京城做官了。
可此后的日子,虽然已有一官半职,但是距离严修的远大理想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他甚至已经打算卷起铺盖回老家跟祖上一起卖盐巴去了,期间他写下了希望“环瀛纵游、退居林下”的诗句。
就在严修觉得自己拼尽全力却够不到一点光的时候,他的人生迎来了又一次转机。
1894年春天,京城的桃花开得正艳,34岁的严修走了官运。朝廷举行了翰詹大考,严修名列二等,获得奖励。
很快,不算年轻但却有为的严修被“组织部门”抛来了橄榄枝,任命为贵州学政。
清朝的学政不仅考文生,也要考武生,因此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每省一员,任期三年。学政主要工作是主持一省学务、考务,带有“钦差”性质,具有专折奏事的权限,相当于现在中央直接下挂的干部。
“贵州学政”这一任命,将已近一潭死水的严修又重新激起了事功之志,他决心通过这次学差,将自己关心的事业——学务改革付诸实践。
今天我们从贵阳去北京,坐飞机只需要3个小时,乘高铁8个小时。而当时北京至贵州的千山万壑,让仅仅只带了14箱书籍的严修赴任之旅花了整整3个月之久。
严修授命之时,正值甲午战争烽火连天。途中,他不断听到前线战败消息,不禁“嗒然若丧”,受到深深的刺激。原本他就对士风之弊有着自己的认识,此时一路观察政情民俗,更促使他进一步反思中国贫弱的原因。他认定“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选育人才要“敦品励学,讲求实用”。
舟车劳顿,刚拍掉身上的尘埃,严修就发布了“观风”“劝学”“申明约束”等告示,表明提振士气、革新风俗的志愿。他告诫学子不要只关心自身前程,更要明白“读书将以致用”,要以天下为己任,探寻国家富强的方略和民生利病的根源。
崇山峻岭难阻干事之心
像个陀螺,严修忙得团团转,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喝杯奶茶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学政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案临本省各府,举行两轮院试,称为岁科两试。巡考期间,还要处理与举贡生监相关的各类案件、事务。
严修有颗面向“星辰大海”的心,纵然贵州崇山峻岭、陡坡弯道也奈何不了他干事业的心,他不避艰难跋涉,遍临贵州各棚考点。繁忙的公务,让他常常一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有一次,他主持考试一整天,深夜还在床上工作,困倦至极,灯花突然点燃被子,险些酿成火灾。
然而严修并没把劳累放在心上,他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转变学风。在时文、试帖之外,他尽可能在部分考试中用策论引导学子通古今之变。比如提问“历代舟师之制”“自唐至明兵制得失”“汉代边防”等,显然是让学子反思甲午战败,乃至晚近积弱之势。他引导学子研究历史上的变法改革,评论战国时的商鞅、赵武灵王,分析西汉贾谊《陈政事疏》 是否可行。
那时候没有“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样的词,但是严修却在做这样的事,他认为,对于西学、洋务不必心存偏见。他让考生“论泰西各国强弱”“论西学之用与用之之法”“论洋务”“论化学之用”,作出自己的思考。他还指出算术在上古属于“六艺”之一,是士的基本素养,今人不可耻习算学。他多次将算学题作为选考内容,鼓励学子加以钻研。
科举考试能否选出有用之才,是严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也反映到考题之中。到任后,他主持的第一场考试,便以“‘科举之士不患妨功’论”为题。这说明他试图找到词章之学与事功之学的平衡点。后来他又以宋儒对科举的讨论为题,问:宋神宗时,王安石和苏轼曾就改革科举进行过一次辩论,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又问:朱熹的“贡举私议”和司马光的“十科举士法”内容分别是什么,能否加以申论。他还曾考查学生对学校、书院制度的了解程度,如问“明代学校之制”“书院之名昉于何时? 历代规制若何?”引导学子反思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八股试帖之学还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严修主持的考试无疑为贵州带来春风扑面。
打开贵州人见识之门
当今中国的论坛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消息今天才从地球传到火星”,因此火星人就是一个信息闭塞的代称。
那时候的贵州人,就是严修眼里的“火星人”。在他与贵阳的书院师生交谈时,发现竟无一人读过 《林文忠公奏稿》《左文襄公奏议》 之类的书籍。直到前往遵义视学,才看到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与上海出版的首期 《时务报》,这使严修深感改变贵州信息闭塞,鲜与外界交往状况之紧迫。
广泛读书是增长见识的方便法门。然而当时贵州连“五经”都缺少善本,不要说其他书籍。为此,严修颇费心思,突然他想起从京赴黔就任时,在湖南武陵遇到贵州籍新翰林谭启端,谭建议在贵州设立书局,购销图书。
这一桩“买卖”让严修想想就激动,在他看来,“有了书本,就有了信息源。贵州就像一个久居深山的老人,几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太需要外面的信息了”。距到任才20余天,严修便说干就干,当即就与贵阳知府文海筹划此事。
然而,随着严修外出考试,此事被耽搁下来。原本设想书局由士绅主持,但遇到阻力。于是严修与巡抚嵩昆协商,改建官书局。开办经费短缺,严修带头捐出养廉银1000两。仅仅70余天,集购运、刊刻、销售于一体,与位于今贵阳慈善巷内原资善堂书肆合并后成立的贵州官书局(后人曾称为慈善堂或贵阳书局),即正式鸣锣揭牌。官书局的开办与运营,不仅疏通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传播的渠道,更是贵州出版印刷事业的发端,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加速新思潮传播
书山有路勤为径,读书才能改命运。在严修看来,学员要有实学,除了多读书、苦读书,没有其他捷径,故他严格“以看书之多寡,作为士子勤惰考察之标准,学官奖惩之参证”。并每月终审阅读书日记、省身札记,对成绩优异者,给以书资与膏火的奖励。以此彰示:只有崇实学,树立良好的学风,学堂才能培养出有用之才。
此外,对学堂设置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大刀阔斧的创新改革。严修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结合贵州实际,在学古书院开设西学课程,宣布就读生员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自己则每天前往学习处督课,遇生员不懂算题时,亲自为其解答。在科举考试尚在进行的年代,这种对书院教学内容及教材的改变,本身就是对旧式教育的一种突破。这对那些一门心思想着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只埋头熟读经史而去应试的生员,无异于当头棒喝,促使他们去学习西学,开阔眼界,以备将来能成为变法强国的有用之材。学员们所经历的这种改弦更张,几乎等同一种脱胎换骨。
甲午之战后,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此时,身在贵州的严修,深切感到改革旧式教育已刻不容缓。正如他在 《复柯逊庵太守》 中所言:“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 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为加速新思潮的传播,他特意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大量购买西学书籍,让学生广为阅读。并再对学堂教学作出进一步改造,亲自拟出32字学堂箴规:“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世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学堂按此要求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之后,逐渐发生了质的蜕变,原来的旧式书院影子渐次消失,新式学堂的形象定格下来。
支持学生建立黔学会
在京城,只要严修愿意,就有着享用不尽的休闲时光,下下棋、喝喝茶、扯一下八卦,一天时间就打发了。而在贵州,严修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能躺平,“学臣有教育人才之责”。他认为:“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非合众不能砺学”。为此,严修决心在贵州省城的学古书院,进行教育改革尝试。
雷厉风行的严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筹备工作从1896年开始,严修就先后制定了书院章程、肄业条约和山长学规,形成了一套规章制度。书院成败在于师资,严修通过长时间物色,决定邀请贵州的经世名儒雷廷珍和懂得西学的郭中广分别担任山长与监院。在传统学问外,书院特别强调算学。为聘请懂微积分的算学教师,严修专门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支援。
路不好走就算了,关键工资还低,无人愿来贵州任教。没请到算学老师,严修便拿起教鞭,亲自上马执教,每日与学生切磋研究。
1897年初,因教授算学的人才缺乏,严修于是电请张之洞代聘通微积分者赴黔任教。张之洞闻讯后,很快为严修送来算学人才郭竹居。郭竹居(字广文),荔波籍,贵筑举人,其父任兴义府学教官时,张之洞曾往受业。
严修订立算学月考制度,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他还支持学生建立起讲学组织——黔学会。在边远的贵州,能够创立自己的学会,与强学会、苏学会、南学会、粤学会等维新团体交相辉映,十分难得。
严修希望学子可以“前不负古人,后不负来者,上不负国家,下不负生灵”。正是有了严修的兢兢业业,到他行将离任时,仅在贵阳参加算课的每月都有几十人,成绩被严修评为超等、特等的为数不少,贵州学子学习数学的兴趣与水准大为提高。更让人惊喜的是,竟然出现贵州向云南输送算学教员的事。
贵州,从向他人求才,到向他人输送人才,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变。
奏请“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明看出了一件事弊大于利,但是又不得不去做,这让严修深陷烦恼。
“八股取士”使得旧科举根本选拔不出国家急需的人才,变革呼声不绝如缕。任学政期间,严修“明知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但由于职任所在,又不得不组织考试。
改变科举的想法一直在严修的大脑中挥之不去,终于,在贵州任内主要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下定决心向朝廷上书“不拘一格选人才”。
严修建议,新科以“经济”为名,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在奏折中,严修还对录取名额、考试周期、推荐保送制度、赴考旅费等环节进行了认真设计,提出建议。奏折最后,他表示,旧科举已经“势处其穷,不得不变”,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推翻,因此可暂时以经济科作为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还是要对科举进行全面改革。
严修奏折呈递后,光绪皇帝指示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进行讨论。转年正月初六日,总理衙门回奏,认为严修筹划周密,当今急需人才,可开设经济特科。当天,光绪皇帝下谕旨同意施行。
严修的建议是在暂时不废科举的情况下,另开特科招纳人才。有研究者将此形容为“保守治疗”,也有人称之为“老树嫁接新枝”。但不管怎样,经济特科的建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湖南巡抚、维新运动的推动者陈宝箴在信中向严修表达敬意,称:“救时之务,莫急于此。”梁启超则直言,此举为“戊戌维新之起点”。
1897年末,时年38岁的严修任满交卸,踏上回京复命的旅程。
严修为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贵州人对其心怀感恩,他临行时,贵州士人路边提酒相送,无不发出慨叹“200年,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杨杰 综合整理《南开大学报·戊戌维新之先声-严修督学贵州始末(陈鑫)》、《贵州历史笔记(范同寿)》、黔中书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
